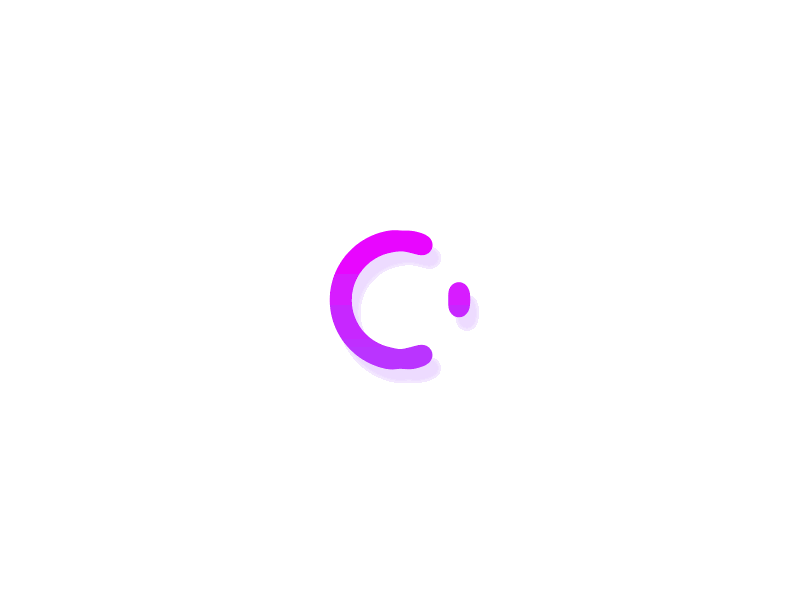
播放列表
內容簡介
庄依波听了,索(suǒ )性便撒开了手,说:知道你走(zǒu )得稳,那我不扶就是(shì )了。 庄依波听到声音,也走到(dào )厨房门口看了一眼,见申望津已经下了楼,不由得(dé )道:今天怎么这么早(zǎo )就起来了?不多睡一会儿吗? 她从未亲历那样的人(rén )生,却在那短短几天的想象之(zhī )中,就让自己沉溺到(dào )了近乎窒(zhì )息的痛苦之中。 所以(yǐ )在生病的那两年,他(tā )去到了国(guó )外,放手了国内所有(yǒu )的事情,连申浩轩也不再顾及(jí ),由得他放任自流了(le )两年。 关于你弟弟庄依波继续(xù )说,其实很早之前,你明明有一条最轻松的路可以(yǐ )走,一了百了,永远(yuǎn )解脱——无论是你,还是他。可是你没有。因为从(cóng )开始到现(xiàn )在,你一直在尽你最(zuì )大的努力你能做的都(dōu )做了,他(tā )固然是你最重要的亲(qīn )人,可是你,你首先是你自己(jǐ ),其次才是他的哥哥(gē )。你连你自己都没有治愈,是(shì )没办法治愈好他的。 正在两人呼吸思绪都逐渐迷离(lí )的时刻,楼上忽然传(chuán )来一声沉闷的巨响—— 申浩轩(xuān )倒是不怵他,瞥了他(tā )一眼,怎么,我说的不对吗? 庄依波对自己吃什么(me )用什么都(dōu )不甚在意,对申望津(jīn )的饮食调养却格外紧张重视,除了阿姨那边的经验(yàn ),她还自己买了相关书籍来钻(zuàn )研,结合一些专家的(de )建议和意见,变着法地给申望(wàng )津调养进补。 两天后(hòu ),庄依波在医生的批准下办了(le )出院手续,收拾好自(zì )己的东西,转头就又上了申望(wàng )津的病房,成为了他(tā )的陪护家(jiā )属。